摘要:中国在经历迅速的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也正步入一个高风险时代。本文从简要评述人类社会风险的历时变迁入手,从社会紧张、社会脆弱和社会不安全3个维度界定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风险",构建了衡量社会转型风险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基于统计年鉴和相关文献提供的数据,具体计算了1993~2004年间的社会转型风险指数,发现这期间社会风险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尤以社会不安全指数的增长最快,但近年来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在高位进入"平台期".最后,作者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特点,从5个方面简要讨论了中国在转型期社会风险快速增长的发生机制。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衡量指标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其人口规模之大、变化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社会矛盾之复杂,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转型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变革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能够解决很多老问题,如中国经济在过去26年中保持了9.3%的年均增长率,国民收入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4.9%上升到2004年的12.9%(World Bank,2005,pp.292~293),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至2004年的2610万;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生态赤字加剧,腐败现象愈加猖獗,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多。诚如邓小平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第1364页)。因此,我们要全面地审视和评价27年来的改革历程,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改革,不能单单看到变革的收益,也要看到变革的成本。
本文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选择以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为视角,通过对转型风险的界定,构建衡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我国社会风险的增长情况,以此剖析转型期社会风险演变的详细版图;在其后的讨论和结论部分,简单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特征以及由此引发风险的内在逻辑,并由此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一、"风险"、"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
对"风险"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而20世纪后半期以来,"社会风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人们对风险的理解并不尽一致,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把风险看作物质特性,强调风险的可计算性;另一则把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强调群体对危险的认知(杨雪冬,2006年,第11~16页)。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风险":一是风险的出现通常伴随着损失的发生,二是损失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损失程度多大都是不能准确预期的,简言之,风险就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人类安全的主导风险是不同的:在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更多时候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先天依赖性,因此,自然风险在人类风险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社会发展进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要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杨雪冬,2005,第87~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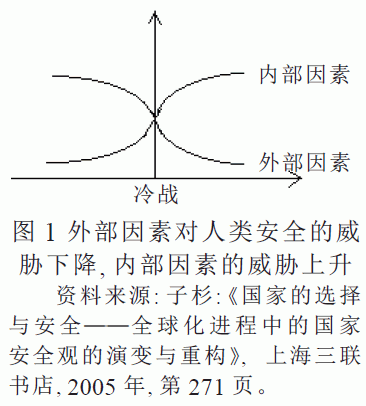
即便是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外部因素的变动也会引起风险结构的改变。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风险是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两次世界大战让整个世界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也让战争阴霾始终笼罩着。但是,由于冷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解体,国家间结构性的冲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外部军事威胁大幅度降低。据统计,从1988~2001年,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杀戮和政治暴力的数量减少了80%(Human Security Centre,2005)。但另一方面,内部风险因素对人类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见图1),成为影响人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各种风险爆发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风险发生的频率急剧上升(丁元竹等,2005,第19页)。
西方学界对现代社会"风险"研究的各类理论范式中,最为系统且影响最大的当推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他们成功构建了以反思现代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早期现代性(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的特征。"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最麻烦的新风险之源泉是绝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认为对我们受益的东西——知识的扩展(乌尔里希。贝克,2005,第42~46页),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吉登斯,1998年,第4页)。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对他们的理论做了大量推介,其中既有著作翻译,也有文献综述「1」,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详细表述。应该说,贝克等人的研究促使对传统"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进展到"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的社会现实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正如该理论的倡导者们所强调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或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人类所处的后工业化、全球化等时代「2」特征的形象描绘。
但是,中国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追赶模式,其发展的起点是较为落后、封闭的农业经济,而目前仍处于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之中,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作为后工业社会分析工具的"风险社会"理论来讨论中国社会的风险结构。换言之,中国当下的社会风险既不完全同于传统的社会风险,更不完全是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时期由知识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会风险,而是多种风险的混合体;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性地存在,即在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出现的风险共生现象(郑杭生、洪大用,2004)。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正进入高风险时代,即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二、衡量转型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计算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指标研究在西方兴起以后「3」,关于社会风险、社会不安的评估指标体系陆续受到了学者的关注。Tirykian(1967)提出了社会动荡发生的经验指标:一是都市化程度的增长;二是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三是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的增长。Estes 和Morgan(1976)提出,一国的社会不稳定程度被认为可从如下6个方面来估量:一是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二是通过标准的统计报告程序所反映的一国内个人需求的水平;三是为满足一国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四是一个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的程度;五是一个社会内部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六是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Estes (1984)又提出,社会不稳定性在下述国家中被认为是最高:一是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二是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三是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少;四是政治上不稳定;五是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六是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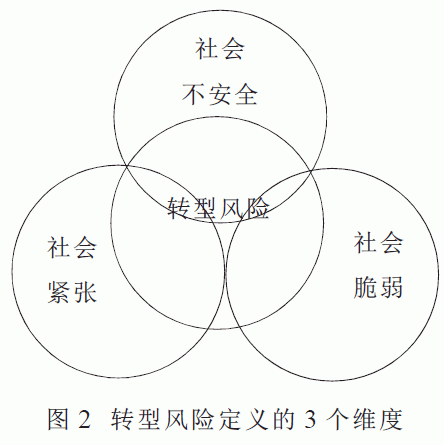
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风险的研究通常与社会预警机制是联系在一起,朱庆芳、宋林飞、阎耀军等学者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朱庆芳(1990)在我国较早地设计出了计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就有关于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的衡量;王地宁、唐均(1991)也随后提出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宋林飞(1995)分经济、政治、社会、自然、国际5个方面,警源、警兆、警情3个层次构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SRSS),并根据可测性、可靠性、充分性、最小性的指标选择原则,从中选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犯罪率、人口流动率等14个指标构成"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之后,宋林飞(1999)将其简化为7大类、40个指标,其中,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与腐败列为警源指标,失业与通货膨胀列为警兆指标,社会治安与突发事件列为警情指标。最近,其又以失业、分化、犯罪、社会不安、社会公害5个维度构建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宋林飞,2004)。
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学者应用社会燃烧理论的有关思想、理想和方法,提出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管理决策系统、民主法制系统等5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稳定与安全预警系统(杨多贵等,2003)。阎耀军(2003、2004)则构建了由生存保障指数、经济支撑指数、社会分配指数、社会控制指数、社会心理指数和外部环境指数6个方面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
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已有的大部分指标体系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甚至许多指标体系缺乏可操作性。这一方面是由社会现象自身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对一个抽象的社会概念而言,对其内涵的挖掘和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与现行的统计体制不健全,社会信息公开度不够,真实性不强有密切关系。因此,许多研究仍然停留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层面,而鲜见有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社会风险表现为多种风险类型的共生共存,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有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风险因素;而在局部意义上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脱离了对这一转型背景的整体认识,就难以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加以深入理解和准确衡量。
为了较为全面地体现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结构的阶段性特征,作者提出"社会转型风险"这一概念。所谓社会转型风险,就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滞后于社会变化,而产生社会损失的可能性。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的社会转型过程: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文明社会、开放社会的转变;从常态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这些转变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新旧事物或新旧机制的更替。但是,这种更替很少是协调一致的,更多时候会出现时间上的错位和滞后,即旧事物被取缔或者不再发生作用了,但新事物却未能及时产生或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更替过程中的"真空地带".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转型风险"分解为以下3个方面(见图2):一是社会紧张,即市场经济催发的竞争意识和趋利意识,促使社会个体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发生经济社会纠纷的可能性增加。二是社会不安全,即由于传统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不再发生作用,但新的安全保障机制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发生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可能性增加。三是社会脆弱,容易受伤害的程度,其通常与贫困或不平等联系在一起(Barbara Harris-White,2002)。尽管社会的脆弱性并不直接表现为社会损失,但其为各类社会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根据上述对"社会转型风险"的概念界定和作用逻辑分析,本文从"社会紧张"、"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脆弱"3个维度来衡量"社会转型风险",并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的原则,为每一类指标分别拟定了具体的衡量指标(见表1)。

"社会紧张"是衡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融洽与否的一个指标,其意味着社会个体在工作、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大小,即社会紧张程度越高,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越大,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越高;反之则反。本文中"社会紧张"程度主要由4个具体指标构成,包括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立案率、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立案率、劳动争议立案率以及离婚率,分别衡量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劳资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需要说明的是,离婚率的持续大幅上升,一方面会带来单亲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更意味着,作为传统道德伦理的重要载体的家庭的解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家庭承担着多项社会功能,包括子代社会化、养老、维系人际关系等等,作为重要社会单位的家庭的解体将引起社会团结程度下降并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社会不安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中将其限定为由外部社会环境因素而引起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主要通过7个指标来衡量,分别为刑事犯罪立案率、治安案件立案率、集体劳动争议发生率、交通事故发生率、火灾事故发生率、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率。在此将传染病和环境污染破坏事故纳入"社会不安全"的范畴,是因为两者都会对不确定的社会人群构成人身或财产威胁,更多时候应以社会危机视之;而集体劳动争议的群体性、对抗性、损害性较强,且很易转化为社会危机事件,所以也作为"社会不安全"的衡量指标之一。
"社会脆弱"是人们平常讨论较多的概念,本文中取4个指标(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加以衡量,一是因为这4个指标学者们讨论和使用较多,二是因为各类文献中关于这4个指标的时序统计数据较为完整。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社会现象的指标衡量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拟采取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萨迪(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从因果分析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整理和综合人们主观判断的客观方法。其优点在于能够将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对复杂问题的决策思维过程条理化、层次化和数量化,有助于简化问题的分析过程,较为准确的获得不同决策要素的权重系数。其基本思想是:先按问题要求建立起一个描述系统功能或特征的内部独立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因素(或目标、准则、方案)的相对重要性,构造出上层某元素对下层相关元素的判断矩阵,以便得到相关元素对上层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序列(Saaty,Thomas L.,1996)。
作者对24位专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请他们对表1中所示的3类二级指标和15个具体指标的重要性(分为"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太重要"和"不重要"5个梯级)进行两两比较,具体方法为:首先,对社会紧张、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脆弱3个维度进行两两比较,由此确定3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其次,通过对"社会紧张"的4个衡量指标的两两比较,确定民事案件立案率、行政案件立案率、劳动争议立案率和离婚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同理确定"社会不安全"、"社会脆弱"的具体衡量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经过对24份回收问卷的赋值处理,最终整合出各类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如表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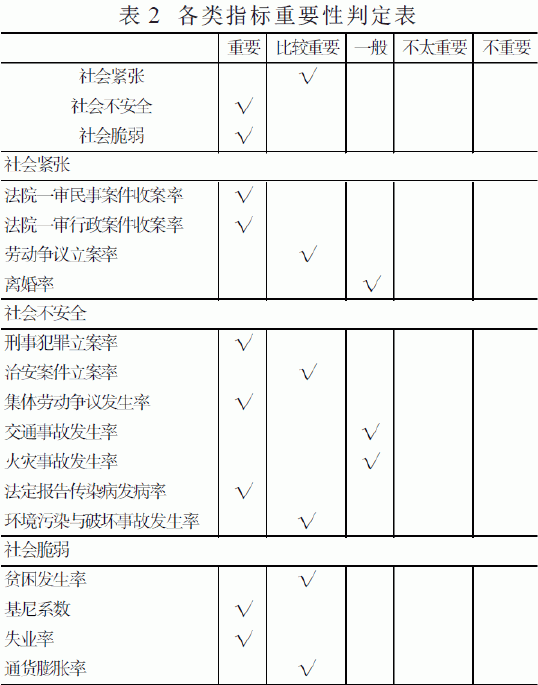
利用logical decisions 软件对表2中的结果进行处理,从而得到下级指标对上级指标的权重,如表3所示。

(三)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以及作者自己关于失业率的计算「4」。除劳动争议立案率和集体劳动争议发生率的分母取该年城镇就业人口数外,其他指标的分母均为年中总人口数。
在计算方法上,本文采取社会统计上关于动态比较的常用方法"综合指数法",具体为:首先根据每个指标在社会风险衡量中的重要程度确定权数,以每个具体指标的增长速度乘以权数相加,得出分类指数;同理,由分类指数乘以相应权数相加,则得到社会转型风险的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R=ΣRxWn /ΣWn×100
式中:R为社会评价总指数,Rx 为单项指数,Wn 为权数。
三、急剧增长: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的衡量结果及分解
(一)快速上升: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趋势
利用上文述及的数据、方法、权重,我们计算了1993~2004年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的具体数值。之所以选择1993年作为本文研究的起点,一方面是因为1993年以来,随着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各类数据较为完整,并且可获得性较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明显地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经济改革阶段和经济转轨阶段(胡鞍钢,2005,第158~161页),其重要的分界就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学界也指出,"改革前"、"改革后"的传统论述语式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是一个与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会,"中国内地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孙立平,2004,第78页)。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随后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上日程,特别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再一次把社会公平问题引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又将出现一些新变化,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讨论1993~2004年期间社会风险的演变趋势就显得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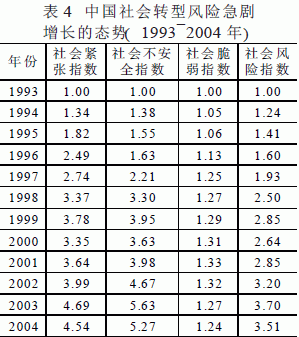
表4列示了我们的计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1993~2004年间,社会转型风险经历了一个急剧增长的过程。以1993年作为基数1,到2004年社会风险指数已经增加至3.51,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1%,高于同时期GDP 「5」的年均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为9.5%),更高于同时期人均GDP 的年均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为8.3%)。在社会风险指数的3个构成要素中,社会紧张指数和社会不安全指数的增长速度最快,2004年分别达到4.54和5.27,且在1993~2004年间呈现出持续的上升态势;社会脆弱指数的增长速度较缓慢,1993~2004年间增长了24%,且在2001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略有回落趋势(见图3)。
如果我们以1997年和2000年为界,将1993~2004年进一步细划为3个阶段,即1993~1997年、1997~2000年、2000~2004年,比较各时期的社会风险增长情况和GDP 增长情况,就会发现,在1993~2004年间,社会风险的增长速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1993~1997年间平均为17.9%,1997~2000年间下降为11.0%,2000年以后进一步降低至7.4%(见表5)。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期的快速增长,社会风险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排除在统计数据上可能出现的误差或不确之处,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征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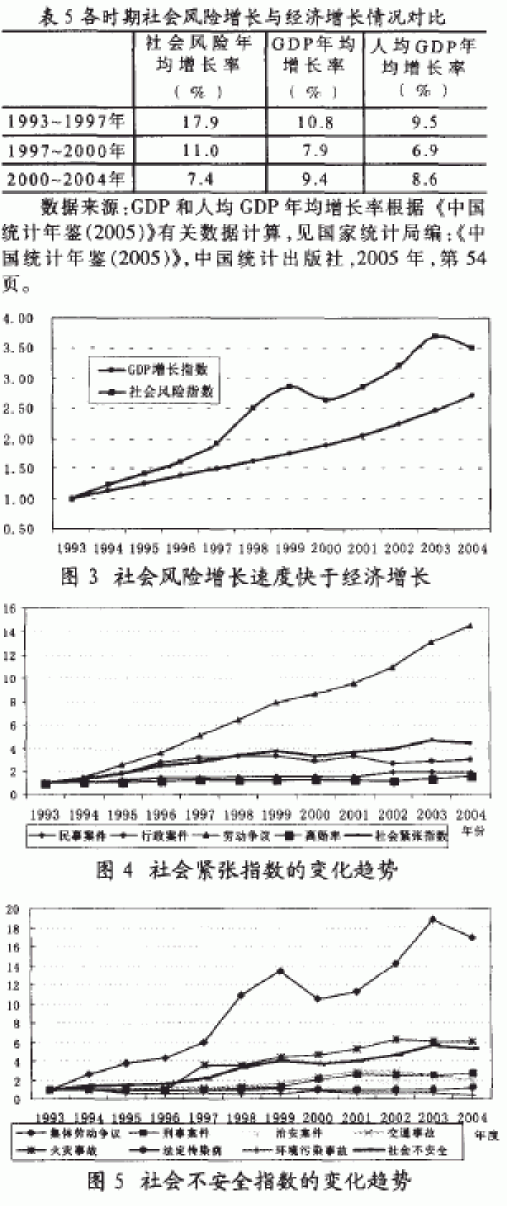
(二)社会转型风险的详细版图
以下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社会紧张"、"社会不安全"、"社会脆弱"3个维度的具体衡量指标的变化趋势,从而勾画出中国社会转型风险增长的详细版图。
首先,"社会紧张指数"在1993~1999年间呈现出持续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24.8%;2000年以来呈现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7.9%.在4个具体衡量指标中,"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率"在1993~2004年间增长了89%,年均增长率为6.0%;同时期,"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收案率"增长了2.02倍,年增长率达到10.6%;"劳动争议发生率"增长了13.8倍,年均增长率为27.7%;"离婚率"增长了67%,年均增长率为4.74%(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劳动争议在过去10多年中呈现出超高速的增长态势,其增长速度几乎3倍于经济增长率;而行政案件也出现了高速增长的现象,10年间翻了一番。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企业职工与企业或企业主(即劳资之间)的矛盾、公众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即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如何实现企业内部、官民之间的融和,达成"劳资两利、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议题。
其次,"社会不安全指数"在1993~1999年间迅速上升,增加了2.9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5.7%,在2000、2001年进入短暂的平台期,随后又持续上升,2001~2004年年增长率9.8%.在7个衡量指标中,"刑事案件立案率"在1993~2004年间增长了1.65倍,年均增长率为9.3%;同时期,"治安案件立案率"增长了80.3%,年均增长率为5.5%;"集体劳动争议发生率"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率为29.3%;"交通事故发生率"增长了96%,年均增长率为6.3%;"火灾事故发生率"增长了5.03倍,年均增长率为17.7%;"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增长了24%,年均增长率为2.0%;"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率"则下降了52.5%,年均下降6.5%(见图5)。
比较之下,集体劳动争议、火灾和刑事案件的增长速度显得更快。特别是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快速增长,已经使我国进入了违法犯罪活动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文森特。帕里罗等,2002,第137页),历次社会调查的结果也都表明,刑事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最大威胁。另外,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增长速度虽然不是很高,但现代疾病以及非典型传染病的出现和蔓延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据统计,在1985~2000年底的15年间,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80例和496例(胡鞍钢、王磊,2005,第40页),而2004年艾滋病患者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项目组,2004),而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人数将为170~270万,由此造成的2002~2015年间每年的GDP 减少1.8%~2.2%(Charles Wolf,2003)。而在降低结核病等传染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方面也落后于几乎所有的邻国。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让我们认识到非典型性风险因素引发公共危机的巨大可能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与近年来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增加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绝非高枕无忧,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系数"(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1.73左右,全世界10个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列倒数第二,接近完全不安全国家之列(丁元竹等,2005,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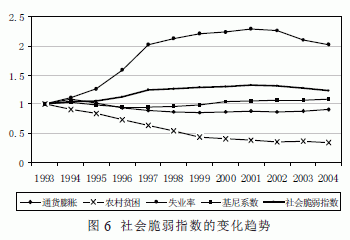
社会转型风险的第3个维度"社会脆弱指数"在1993~2004年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在2001年左右达到峰值,2001年以后的下降主要起于失业率和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控制「6」。具体而言,农村贫困发生率自199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8.4%降至2004年的2.8%,减少了67%;失业率在2000、2001年左右达到高峰,之后逐渐下降,2004年约为7.5%;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达到峰值(24.1%),之后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在个别年份里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情况,对保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社会总体稳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2003年达到0.453,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和分化将是当前中国各类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引发各类危机的最大风险所在。作者对专家的调查也体现了这一点,因而在15个指标中对基尼系数的权重分配也是最大的(0.1332)。
四、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机制分析
(一)经济转型的社会特征
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风险,需要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大背景。27年的经济改革和积累,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
(1)社会流动性增强(这里主要指水平流动)。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以及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促使中国从相对静止的社会变成流动的社会。1994年国内旅游人数为5.24亿人次,2004年上升到11.02亿人次,10年之间翻了一番。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数从1994年2.05亿人次,增加到2004年4.59亿人次,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数由1994年3.19亿人次增至2004年6.43亿人次(国家统计局,2005,第173页)。1994年出外打工的农民工人数约为4400万人,到2004年提高到1.46亿人。
(2)社会原子化。经济体制转型使社会公众的就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单位和家族在民众生活中渐渐失去了主导作用,中国从一个总体性社会逐渐向原子化社会演变。1978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就业人口中90%以上在正规部门,而目前在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外资企业等正规部门就业的人数只有1亿人,有1.6亿人属于非正规就业。
(3)社会分化程度加剧。中国在过去10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财富,但财富的分配已经从平均主义模式转向"超富"阶层的兴起(Jonathan Anderson,2005)。据世界银行估计,198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未经过城乡居民生活费调整)为0.28,1990年上升为0.35,2001年为0.45,比1982年上升了60.7%,比1990年上升了28.6%(Martin Ravallion,Shaohua Chen,2004)。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分配尤甚,全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55(李实、魏众、丁赛,2005)。
(4)社会开放度升高。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让中国社会从相对封闭的形态走向不断开放的形态。1990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00万人次,2004年已经达到1.1亿人次,相当于世界总数(7.6亿人次)比重的14.5%;中国居民出境人数则从1998年的843万人次,上升至2004年的2885万人次,6年间增加了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3%.
(二)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机制
上述变化一方面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活力,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挑战,导致社会风险因素的不断增加。
首先,不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导致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发生社会抗拒行为的风险增大。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既是快速的,也是不均衡的,一部分精英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群体;而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却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同时,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属于"渐进式"改革,改革的收益通常是立竿见影的,但改革的成本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造成了改革成本的延期支付现象。掌握优势资源的受益群体更容易利用这一特点把本应自己承担的成本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这种不公平的成本分担形式导致改革的利益受损群体产生了较强的被剥夺感,在缺乏合理的、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容易积聚下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威胁。
其次,社会流动性(人员流、资本流、信息流等)和分散化的提高,使社会个体之间、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增加,社会交易成本上升,社会治理的难度在增大。20多年的转型过程使中国社会迅速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是重复博弈,而越来越像一次博弈,从事越轨行为的机会增多,而越轨之后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减少(胡鞍钢、王磊,2005)。另外,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对城市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造成了巨大压力,城市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人口拥挤现象比较严重,流动人口对城市资源的压力在增加,与城市原住居民与其在工作、生活中利益矛盾冲突在增加,爆发各类传染疾病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扩大了风险的来源,使中国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高风险时代".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使中国从中受益匪浅,但是经济的全球化和风险的全球化是同时发生的,这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还包括非传统的风险因素,如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经过数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防范风险和危机的较完备的体系;但中国却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来面对与这些国家同样复杂甚至更复杂的问题,这无形之中进一步加大了风险发生和扩散的可能性。
第四,风险应对与缓冲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各类社会不安全因素增加。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和家族承担了大部分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功能,在社会个体和风险之间构筑了一道防护层、缓冲带,对社会个体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但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逐渐丧失了,而新的社会保护机制迟迟没有形成,社会个体不得不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风险。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虽然中国的失业率与欧洲接近,但是"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有良好的社会安全体系来保护工人"(高盛公司,1999)。
第五,风险自身的特性加剧了风险爆发的可能性。风险的发生并不是一维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即一种风险发生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和控制,很容易引发其他的风险,造成不同风险的叠加效应。印尼即是一个典型案例。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印尼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是为世界所瞩目,但当其突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先是引发国内经济危机,接着演化为社会危机,然后爆发政治危机,苏哈托政权随即垮台,整个国家从危机走向社会动乱,GDP下降了20%以上,人口贫困发生率从危机前(1997年5月)的15.4%突然上升到危机高峰(1998年8月)的33.2%(Hadi Soesastro ,2005)。其他国家因金融风险导致社会危机或因社会风险导致政治危机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五、结论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转型过程,"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都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重大议题。本文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分析,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一国的内部风险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主导因素,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主要由社会紧张、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脆弱3个维度构成。而在具体的衡量指标体系中,经过专家意见调查,贫富差距、失业率、刑事案件、集体劳动争议、传染病成为决定社会风险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指标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权重。
2.在1993~2004年间,中国社会的转型风险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这一时期风险指数增加了2.51倍,年均增长率为12.1%;但另一方面,社会风险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逐渐减缓的迹象,预示着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社会风险将进入一个平台期。
3.社会不安全和社会紧张的增长速度较快,是社会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而社会脆弱指数则由于实际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下降,在2000年以来出现了回落迹象,但基尼系数的不断增大是困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4.经济转型过程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流动性增强、开放度提高、分化程度加深以及社会成员的原子化等特征,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风险的来源、加剧了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性、引发了社会不满,再加上风险应对和缓冲机制的确实以及不同风险之间关联叠加的特性,促成了中国在转型期间社会风险的迅速上升。
当然,本文在分析和论述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转型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际计算。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础所在。但是,社会风险这类综合性的抽象概念,应该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与公众的主观心理进行综合评判,不能局限于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也同样重要。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人们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有较大影响,人们对不满的表达呈现出跳跃式突进的特点,即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即便有不满情绪也会忍着,当忍无可忍的时候,又会以较为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本文的研究主要仍是基于客观指标的分析,因此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另外,关于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机制,本文也未展开详细的实证分析,作者将另具文论述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1」对西方学界关于"风险社会"的具体阐释,本文不做具体的列述,可参见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53~59页;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87~90页。
「2」吉登斯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风险的存在,这个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社会指标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 )于1966年在《社会指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关于社会指标的概念及其发展,可参见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4」关于失业率的数据参见胡鞍钢、盛欣:《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及背景分析(1995~2003)》,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工作论文,未刊稿;其他年份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估算而得。
「5」本文使用的GDP 和人均GDP 数据,均是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一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重新核算和修订后的数据。
「6」本文所用的"失业率"是实际失业率的概念,而非政府统计中所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and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92~2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3)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5)Human Security Centre ,Human Security Report,2005,War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6)丁元竹等:《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8)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
(9)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0)Tirykian E.A.,1967,"A Model of Social Change and ItsLead Indicators ,in Klausner S.(ed.by )",The Study of Total Societies,Garden City ,New York.
(11)Estes Richard J.and Morgan John S.,1976",World SocialWelfare Analysis:A Theoretical Model",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19(2):pp.3~15.
(12)Estes,Richard J.,1984,"The Social Progress of N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3)Barbara Harris-White,2002,"Globalization,Insecuritiesand Responses :an Introductory Essay",In Barbara Harris-White ed.Globalization and Insecurity:Political,Economic and Physical Challeng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p.3.
(14)Saaty,Thomas L.,1996,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Planning,Priority Setting ,Resource Allocation,RWS Publications.
(15)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6)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
(18)胡鞍钢、王磊:《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与社会治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2》,2005年。
(19)国务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中国艾滋病项目组:《中国艾滋病预防、治疗及关怀的联合调查报告》,中国政府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项目组,2004年。转引自世界银行:《中国在卫生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中国国情分析报告》,2005年第17期。
(20)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
(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
(22)Jonathan Anderson,2005,"How Serious are Socio-EconomicTensions?",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Asian Economic Perspectives,15August.
(23)Martin Ravallion,Shaohua Chen ,2004,"China's (Uneven)Progress Against Poverty",World Bank ,June 16.
(24)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25)胡鞍钢、王磊:《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双向效应》,《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6)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1999年9月21日。
(27)Hadi Soesastro,2005,"Poverty in Indonesia",CSIS,Indonesia,Apr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