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引导制造业回流,重振实体经济。同时,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特别是福耀玻璃投资美国等事件引发有关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差距的热议,而此前一些国外咨询公司如波士顿咨询公司连续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逼近发达国家水平,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究竟处于什么水平?笔者通过比较1990—2015年中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认为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确存在此消彼长的态势,导致我国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持续弱化。
一、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1. 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1990—2015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2073元提高到55324元,16年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6倍。同期,美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28173美元上升至55292美元,劳动力成本仅上升了1.9倍。值得注意的是,汇率波动也是影响中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由1990年的4.8上升至2000年左右的8.3,又逐步降至2015年的6.2。考虑汇率因素后,若统一按人民币计价,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距一直在缩小,而且这种趋势在2008年之后更为显著。1990—2015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几乎一直高于美国,美中制造业平均工资差距已由1990年的65倍降至2015年的6倍。
2. 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超过中国,吸引制造业的区位优势凸显
1990—2015年,美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上升了3.16倍,而制造业人均工资上升了1.91倍,这使其劳动力成本产出比由1.98上升至3.27,即每支付美国制造业工人1美元,可以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由1990年的1.98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3.27美元。相比之下,同期中国制造业人均增加值虽然提高了24.73倍,而由于同期制造业人均工资上升26.69倍,导致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不升反降,由2.59降至2.40,即每支付中国制造业工人1元人民币,可以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由1990年的2.59元降至2015年的2.40元。与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一直稳步增长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驼峰”式变化过程。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自2008年起,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已低于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可通过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化”其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反观中国,自1997年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只能勉强“跟上”劳动力成本增速,劳动力成本产出比止步不前。随着2008年后制造业人均工资进一步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产出比甚至出现下降。因此,从制造业总体来看,目前投资美国已比中国更具“性价比”,这也是部分美国企业回流本土、一些中国企业“出走”美国的重要原因。
3. 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地区间差异较大,其相对“落后”地区与中国的差距更小
进入21世纪,金融部门膨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美国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美国各州之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以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哥伦比亚特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几乎是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内布拉斯加州这些所谓“落后”地区的两倍。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地区差距则显著低于美国。江苏、广东、浙江这些沿海地区工资仅比西部的陕西、甘肃、宁夏高10%~20%,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明显。由于2015年美国“落后”地区45000美元左右的平均工资较全美平均工资55292美元还低近20%,其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差距更小。再考虑到美国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加之美国部分州政府为吸引外国投资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产出比优势将更为突出,或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首选地区。
4. 中美新兴产业劳动力成本均享有“溢价”
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是中美共同特点。以ICT (信息通信技术) 产业为例,2015年美国ICT产业人均工资达到67204.8美元,是制造业人均工资的1.25倍,而中国ICT产业人均工资达到112042元人民币,是制造业人均工资的2.03倍。可见,对ICT这种新兴产业而言,人均工资比制造业平均工资高是正常现象。然而,相比美国ICT产业工资溢价倍数一直稳定在1.20左右的水平,中国ICT产业由于起步较晚,人均工资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更大,但随着时间推移,ICT产业工资溢价倍数不断下降。这表明,对ICT这类新兴产业,在产业发展初期为了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会给予高于传统行业的工资,但当产业逐步进入成熟期后,其与传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同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效果初步显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成果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这些新兴产业在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阶段往往对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现阶段,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而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对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因此,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对新经济发展并不具备吸引力。
二、几个判断
通过以上中美劳动力成本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对差距逐步缩小,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高出中国,并对投资者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成本攀升,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由逐步弱化加快转为系统性减失,已经接近临界点,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并发挥作用,在很多领域发展动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创新步伐加快、新兴产业群体性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中国制造”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是尽管中国制造业成本明显上升,但成本上升并未带来应有的福利效应。就笔者调研中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住房等生活成本大幅攀升,生产企业的一线员工普遍感受不到与工资上涨同步的福利改善。加之运营中遭遇的其他困难,进一步挫伤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在国内坚守实体经济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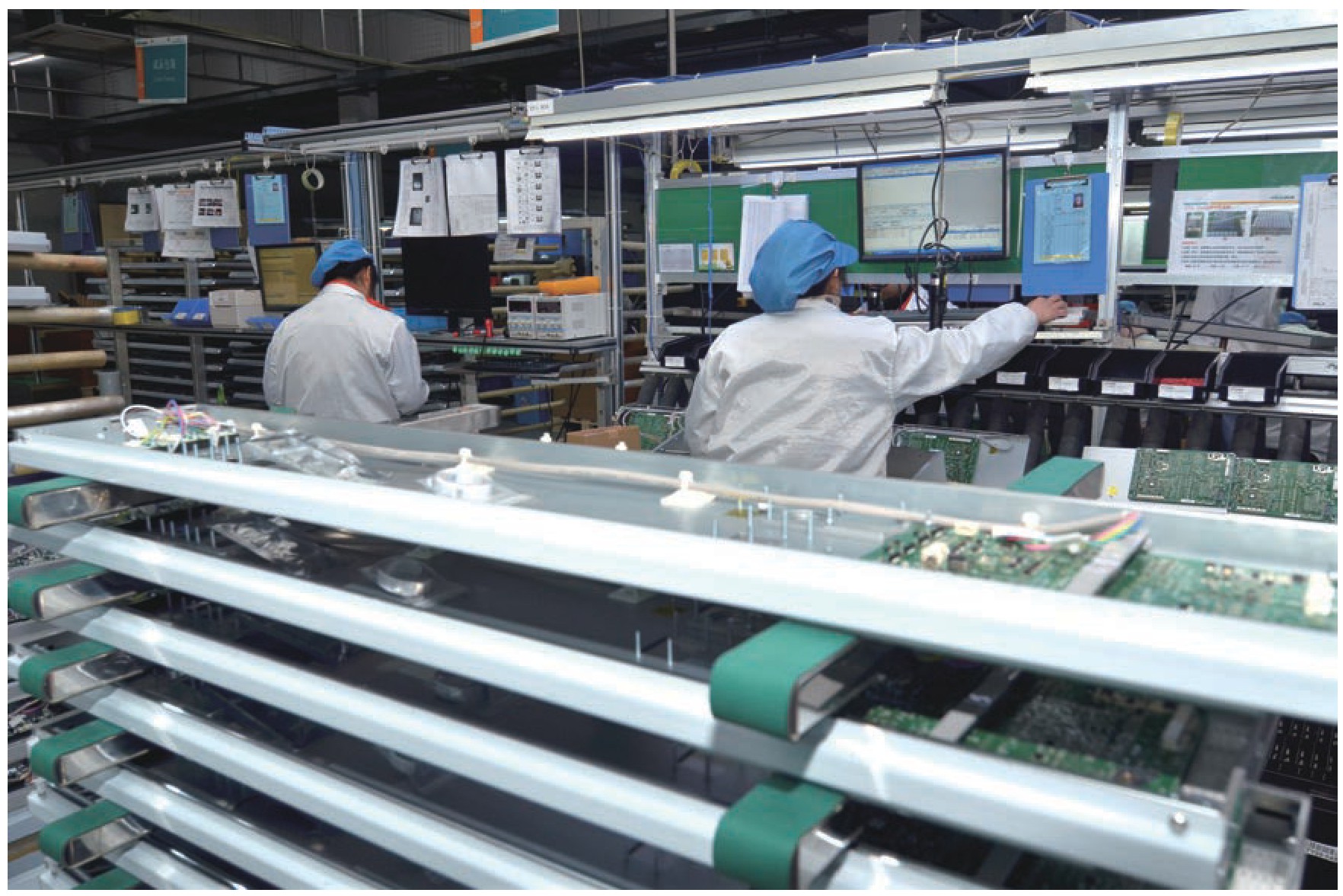
三是目前美国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虽然仍高于中国,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制造业日益智能化、数字化,将对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结构带来新的影响。可以预判,美国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抵消其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差距。
四是中美劳动力成本此消彼长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受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94年启动的汇改下,中国人民币快速贬值,致使美国劳动力成本相比中国陡增,而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成本。进入2016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如果后续保持贬值预期,则有利于短期内抑制国内劳动力相对成本上升的态势。
五是国外一些咨询公司发布中国制造成本变化趋势及其与主要国家的比较结果,虽然引起了关注,但总体来看,有关部门对这些报告结论的舆论效应重视不够。以波士顿咨询公司为例,其公开发布的研究报告形成了一定的投资引导作用。由于全球主要大跨国公司都是其客户,尽管部分测评结果并不严谨,甚至是错误的,却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区位决策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六是从人口规模和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各类制造行业仍有巨大市场和发展空间。劳动力成本优势持续弱化引发的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势必对国内就业形势和地方经济发展产生冲击。为此,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用脚投票”的投资决策,特别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撤离中国,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要高度警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避免因经济过快“脱实向虚”导致中国制造“未强先空”“快盛快衰”。
三、对策建议
1. 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配合《中国制造2025》全面实施,协同扩大对外开放、深化流通领域改革、知识产权保护,集成生产要素、国内需求、产业聚集、技术能力等硬件条件以及国家价值观、历史、文化等软实力,加快培育形成以技术、品牌、服务、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迈上绿色化、智能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加大投入力度,鼓励一些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或差距不明显的领域开展颠覆性创新,引导企业投入商业模式和产业化创新,推进重点突破,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拓展投资项目储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投资者进入国内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机遇和选择。
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企业降成本
一要坚持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延展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二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加快工业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建设绿色智慧工厂和产业园区,引导企业开发使用工业机器人,提高企业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通过“机器代人”,改善企业成本结构。三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着力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4. 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
在稳定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创新投入机制,引导多元化资本和机构参与,完善多层次培训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技能竞赛,强化激励,积极倡导爱岗敬业精神,切实提高劳动力素质,打造知识型专业技术人才和技工队伍,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匠精神和制造文明,逐步将中国制造带入技术进步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5. 完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有序转移
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家有关落后地区开发政策支撑体系,对中西部地区在财税金融、用地规划、市场准入、教育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实行合理有效的倾斜,尽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充分释放差别化的政策效应,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国内外投资的吸引力,扩展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