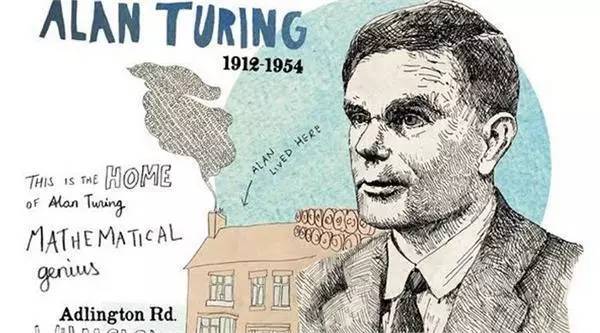
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绕不开的首要问题就是其与人类智能的关系。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的先驱阿兰·图灵(Alan Turing)在1950年“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提出的“图灵测试”,即通过机器对人类语言的“模仿游戏”来测试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在1980年提出的“中文屋”问题,则从图灵测试的反面进一步思考“智能”的本质:如果能够通过英文对照的中文字形手册,手写回答所提出的中文问题的答案,即使测试者不懂中文,在观察者看来也和完全掌握了中文一样。这个哲学上的假设原本的意图是揭示“智能”与“意识”的关系:所表现出的智能行为是否需要主观意识活动的参与?“无意识”是否是智能?由于其涉及如何判断何为“智能”这一根本问题,因而也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著名问题。无论是图灵测试还是中文屋问题,其默认的隐含条件是:智能即人类的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评价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它能否能够模仿人类,而模仿不仅包括对行为的模仿,还应包含行为背后的“动机”的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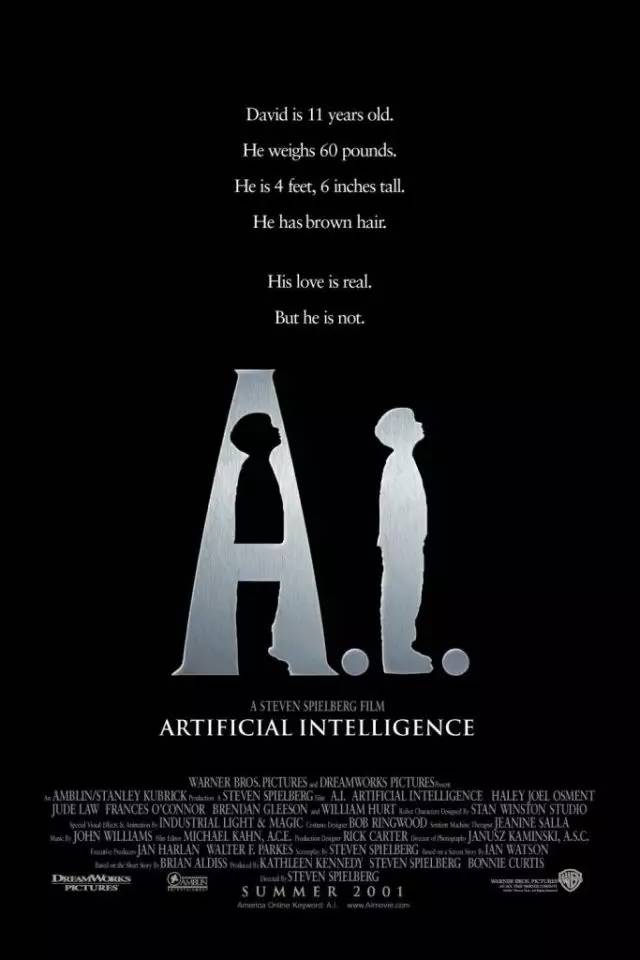
人性=智能?
在斯皮尔伯格2001年拍摄的电影《人工智能》中,机器小男孩David被赋予了人类爱与被爱的情感,替代一对夫妻失去的孩子。然而一旦真正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David立刻遭到抛弃被送往机器人屠宰场。模拟人类的情感,在机器世界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多余,构成了一种道德的两难困境,越是像人,困境越深。人工智能一旦具有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诉求,“机器权利”的话题就会随之而至,热播的美剧《西部世界》就深入刻画了这一主题:人性的堕落反衬倒是使机器更具人性,更像人,那应不应该受到像人类一样平等的对待呢?至少,好莱坞的编剧已经使观众情感的天平偏向更“像人”的机器。人工智能是要复制出具有“人性”的人类自我镜像?亦或应该是创造具备人类优点又超越了人类存在的新的物种?据此去理解,人工智能的最终意义将是:人类像创世纪的神灵一样,依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一批子民,这些子民最终拥有自我意志并“杀死”自己的创造者。这就像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在《智能的本质》的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机器终将取代人类的论调,即所谓的奇点论,其本质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语境,成为了后宗教时代的新宗教。[1]“信**,得永生”是戏谑邪教的标准句式,而这个句式,套用在奇点论中竟然毫无违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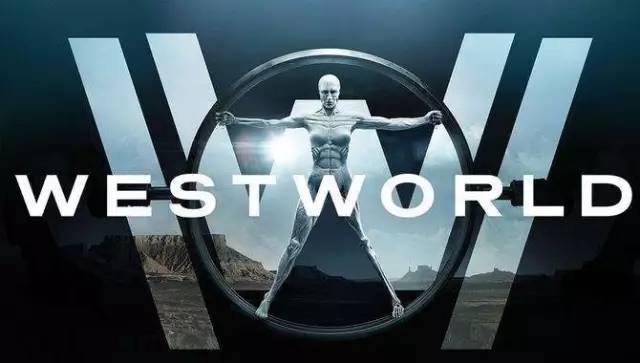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与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在2016联合发布了探讨机器伦理(Robotics Ethic)的报告(草案)。[2]报告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人与自动化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平衡机器制造者、销售者和最终使用者的责任分担机制的问题。相比“人性”的机器带给人类的困扰,更为迫近的困扰来自于“人性”本身:如何才能保证由人编写的算法代码中不含恶意?如何才能避免来自于每个人的数据资源成为制造垄断利润的工具?如何才能让人真正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给“无法理解”的机器?显然,连人类自己都无法掌控的复杂和多变的“人性”,附加给机器不仅很难实现且毫无必要。机器的准确和高效正是用来弥补受生理、情绪等影响而不可控的“人性”,而具有“人性”的机器,显然并不能从“智能”的角度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帮助。
模拟=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中的Artificial,其含义是“人工的,人造的,非自然的,虚假的”等,实际上并未包含“模仿”或是“模拟”的含义,中文翻译所对应的“人工”也同样如此,然而标志着人工智能重大进展的事件却总来自于对人的行为的模拟。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与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在2009年所著的影响广泛的人工智能教材中[3],从内在和外在表征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四种不同定义:像人类一样思考的系统;像人类一样行动的系统;理性思考的系统;理性行动的系统。其中将“理性”作为鉴定人工智能的标准之一。遗憾的是,何为“理性”与何为“智能”一样,同样边界模糊——脱离了“人类”去定义“理性”甚至比脱离了“人类”去定义“智能”更加匪夷所思:我们能够理解动物具有某种智能,比如大猩猩会使用工具,实验的小鼠能够通过奖励与惩罚“学习”某种能力,以及昆虫、鸟群、鱼群等呈现出的“群集智能”,但却无法想象这些动物可以具备“理性”——逻辑推理是否就等同于“理性”?从1997年IBM“深蓝”首次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帕斯特罗夫开始,到从去年热炒至今的AlphaGo横扫围棋棋坛,“人机大战”总是能赚足眼球:媒体的渲染下犹如两个物种之间的决斗。然而棋盘两边执子的都是人,并且AlphaGo运行着人为它编写的算法。所谓的“人机大战”,其实恰好表明了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莫拉维克悖论” (Moravec's paradox):“要让电脑如成人般地下棋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让电脑有如一岁小孩般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人类智慧所独有的逻辑推理等能力,只需要很少的计算能力;而无意识的本能、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计算能力[4],正如AlphaGo可以通过Google的TPU每秒进行数百万亿次运算来推断每步棋的输赢概率,却依然无法完成自己走棋这样几乎不需要智力的简单行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发展建立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而人类自身却是数十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的奥秘依然知之甚少,因而目前的人工智也仅能模拟那些已程式化和结构化的思维过程,比如逻辑推理。

然而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解决问题的时候,却总有那么一些似是而非:比如将围棋的直觉和判断转化为输赢的概率计算;比如将对翻译中对语义和语法规则的理解转化为大规模的词汇和短语的匹配。这些计算和匹配,是否就等同于“模拟”了人类的思考和智能呢?丹麦计算机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机器是否能思考,与潜水艇是否能游泳的问题很像”——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模拟,并不是完全形神兼备的复制,即使是人类自身的机制也还有太多未解之谜,人工智能需要通过全新的形式来定义和表达智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模拟仅仅是最初的第一步。
计算=智能?

2006年,会议五十年后,当事人重聚达特茅斯。左起:摩尔,麦卡锡,明斯基,赛弗里奇,所罗门诺夫
1956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夏季会议上,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被称之为“人工智能之父”。他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制造智能机器,特别是智能电脑程序的学科和工程;它与通过电脑研究人类智能的过程相关,但却并不局限于生物学成果的应用。”[5]而“智能是在环境中通过计算实现目标的能力,不同类型和级别的智能存在于人类、许多动物和机器上。”[6]他同时也认为,目前并没有脱离了人类的智能去理解智能的绝对定义,原因是“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什么样的计算过程可以从整体上被称之为智能,我们目前仅了解部分的计算机制而不是全部……一些程序只能说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智能。[7]
由此看来,“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也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是一个很难准确定义的概念,而这一点其实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已由阿伦·纽维尔(Allen Newell)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然而从图灵设计出通用的计算机器,到AlphaGo以绝对优势战胜世界排名第一棋手的柯洁,在这80余年中,人工智能从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到现在几乎渗透至各个行业底层的“计算能力”,其依据图灵机进行通用计算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据此,智能=计算,人工智能=机器计算的等式俨然已经成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大数据爆炸式增长和硬件遵循摩尔定律发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的研究核心集中在机器学习领域。掌握学习的能力就等于掌握了智能不断增长发展的能力。机器学习算法按照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在《终极算法》(The Master Algorithm)[8]中的归纳,分为5个不同派别,分别是:符号学派,将学习看作符号表达和逻辑推演,主算法是逆向演绎;联结学派,认为学习需要模拟大脑神经元的机制,主算法是反向传播;进化学派通过模拟遗传学和生物进化来设计算法,即遗传算法;贝叶斯学派,专注于运用贝叶斯概率推理,朴素贝叶斯算法和贝叶斯网络为其主要算法;类推学派,通过对事物相似性的外推来进行学习,主算法是支持向量机。这五个学派的源头来自于对人工智能的两大不同设想,一是通过逻辑表达概括人类思维的过程。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早期人工智能专家通过符号的逻辑推理来设计人工智能,并开发“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等人工智能早期应用,即属于此种设想的延伸。二是以生物学的视角模拟人类思维的产生。1943年: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发表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9],建立了神经元模型;此后,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在1958年构建了首个由两层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即“感知机”(Perceptron)。在新千年由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热潮兴起时,由逻辑推理构建的“专家系统”和“知识库”已经被淘汰和遗忘,倒是之前受计算能力限制而未被重视的神经网络,开始焕发勃勃生机:语音识别、机器视觉,以及大名鼎鼎的AlphaGo,都由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所支撑。
然而不论是借道于人性、模拟还是计算,最终很大可能将是殊途同归。多明戈斯在《终极算法》试图结合机器学习5类学派的优势,设计出一种能够通用解决各类问题的Master算法。按照他的分析,5类学派的方法最终都能简化为逻辑的方法或概率的方法,而他所认为的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马尔科夫逻辑网络”,将有可能是最后的Master。实际上,目前的人工智能运用领域已是多种算法相互融合的结果,如AlphaGo就运用了深度神经网络来进行自我对弈,再通过蒙特卡洛搜索优化贝叶斯网络计算获胜概率。也许能够适应一切应用环境的“终极算法”(Master Algorithm)或是“元方法”(Meta-solution),将会是朝着人类既渴望又惧怕的具有“人性”的“通用人工智能”迈出的关键一步。但是正像前文所指出的,由于在“人工智能”的定义中,对什么是“智能”在本质上缺少整体的界定,目前所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仍未超越通过图灵机的数学方法解决单一问题的范畴。麦卡锡曾经感概:一旦用人工智能解决了某一领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再被视作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认识“智能”本质的过程很像一个“去魅”的过程,正如看来稀松平常的机械自动化,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是“魔法”一样,一旦运用计算机的数学运算实现了某些“智能”的行为,这些行为看上去就显得不太“智能”了。
机器+计算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人们对智能的本质进行探索的一条路径,无论是“智能云”还是作为基础设施的计算平台,依然是自动化工具的延伸。既然我们依然无法从整体上定义智能,那么关于人工智能的探索,除了机器计算之外,至少也应该在充分融合了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前沿之后,再去寻求更加恰当与合理的定位。“哲学”曾作为探究世界规律的入口,孕育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人工智能”可能将是人类理解自身和生命终极奥秘的入口——这个入口,理应更加宽广。
[1]《智能的本质》(Intelligence Is Not Artificial):[美]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Scaruffi著,任莉、张建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
[2]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55/245532E.pdf
[3]Stuart Russell and Peter Norvi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3rd Edition) (Essex, England: Pearson, 2009)
[4]http://baike.baidu.com/item/莫拉维克悖论
[5]It is the scienceand engineering of making intelligent machines, especiallyintelligent computerprograms. It is related to the similar task of usingcomputers to understandhuman intelligence, but AI does not have to confineitself to methods that arebiologically observable. http://www-formal.stanford.edu/jmc/whatisai/node1.html
[6]Intelligence is the computational part of the ability to achieve goalsin theworld. Varying kinds and degrees of intelligence occur in people, manyanimalsand some machines.
[7]The problem isthat we cannot yet characterize in general what kinds ofcomputationalprocedures we want to call intelligent. We understand some of themechanisms ofintelligence and not others… Such programs should be considered``somewhatintelligent''.
[8]《终极算法》(The Master Algorithm):[美] 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Domingos)著,黄芳萍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
[9]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5:115-133,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