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李兴成所领的75两退押银以及分得的9石谷,是供其偿债的全部资产。债主们念及其生活极度窘迫,同时还有赡养母亲的责任,因此允许李兴成以摊还的方式偿还债务。为保证摊还过程的公开透明与诚信无欺,债务人李兴成请来了团甲、业主及债主们,一方面是为清算净资产,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无力偿债寻求同情。果然,债主们“垂怜”李兴成母子,准许他们在净资产的基础上,留取15两的生存资本与养赡银,然而再把余银60两按照20%的比例,来偿还300两的债额。
摊还是以公开商议及谅解为前提的偿债机制,李兴成关于债务及摊还的叙述是可信的。债权人之所以能够忍受20%的本金回收,主要是顾及了债务人的生存权利。这表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生存伦理对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前文案例比较,似乎李兴成作出的摊还决定是由债务人、债权人及团甲等三方协商的产物,但令人不解的是,张吉安为何没有当场拒绝摊还呢?结合当时的情境来考虑,迫于舆论道德的压力,张吉安不可能违背多数人的“允摊”意见,而表达个人的债权诉求。
(二)利与义的博弈
李兴成描述了自己摊还债务的身不由己以及诸多债权人的“垂怜”之恩,这与有意抵制摊还且强行逼债的张吉安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张吉安的逼债过程,田华轩在其辩词中有着详细的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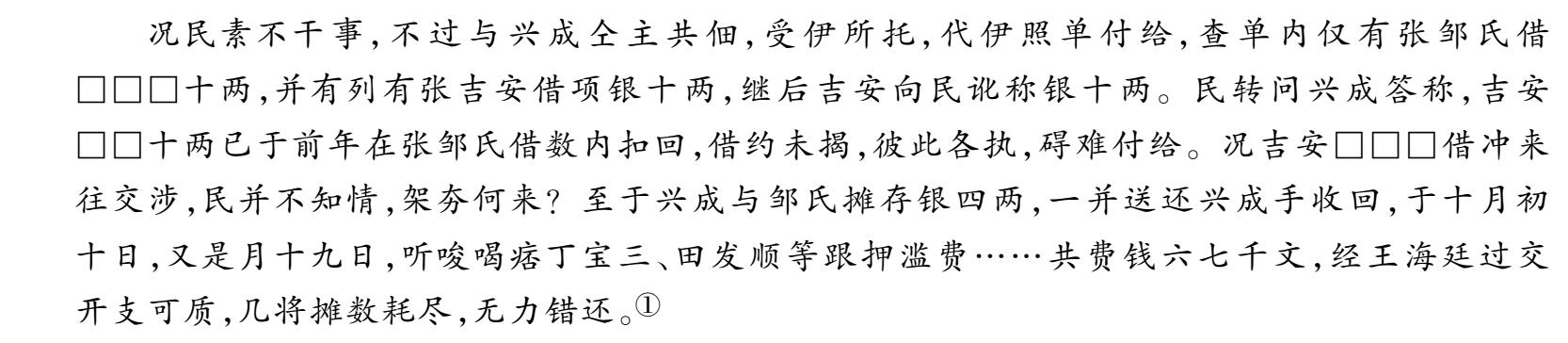
被告田华轩的辩诉内容有三点:其一,张吉安告他无理,因他与债务人李兴成仅是伙佃的关系,且代李兴成处理摊还问题,所以即便张吉安对摊还不满,也不应迁怒于他。其二,张吉安在借贷过程中存有“见利忘义”的私心,经他介绍而向张邹氏借到银20两,但或许是由于极度怀疑李兴成的偿债能力,所以他擅自扣留了张邹氏银10两,作为李兴成归还给自己的本金。这样一来,张邹氏与李兴成之间事实上只存在银10两的借贷关系。当李兴成沦落至唯有通过摊还方可以还债的境遇时,他认为李兴成应再额外补银10两才能罢休。田华轩将张吉安的动机视为“讹诈”。其三,张吉安为追债不择手段,“喝痞跟押”导致田华轩耗费“钱六七千文”。
从契约上看,李兴成确实借了张邹氏银20两,按两摊还,则张邹氏仅可得银4两。张邹氏拒领摊还银两,要求担保人张吉安清偿。张吉安同样不愿承担借贷风险,因此状告中人田华轩与债务人李兴成。对此,田华轩和李兴成的辩词始终强调,李兴成实际只借到张邹氏银10两,因为担保人张吉安从中扣银10两。这也是本案令人费解的一点:既然是摊还偿债,无论谁的债,都应按照摊还规则一一还债,那么原被告为何要在借资是“10”或“20”两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呢?
结合张邹氏之本金、利息与摊还金额信息可知:本金银20两,两年生利谷16斗,折银约5.28两,摊还金额为4两,则张邹氏之债权损失率约53.6%。田华轩与李兴成之辩词表明,被张吉安所扣的银10两,作为退还张邹氏之银10两,那么向张邹氏实际的借贷本金仅为10两,两年生息8斗,折银约2.64两,摊还金额为2两,则张邹氏之债权损失率同样为53.6%。无论是借银10两还是20两,张邹氏的本利都将损失53.6%。但问题在于,张吉安是担保人,他有责任弥补摊还所侵蚀的债权利益。如果是借银20两,张吉安要补银16两,如果是借银10两,则仅补银8两。金额越大,担保人张吉安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就越大。田华轩反复强调借银10两而非20两,暗示了担保人因承担风险而遭受16两的巨大损失,确实不妥。
张吉安不愿承担全部风险与损失,但在以熟人为主的乡村关系网络中,他很清楚,李兴成母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按照斯科特之观点来看,处于生存安全临界线的农民,早已经不得半点索取。如果张吉安继续咄咄逼人的要求李兴成母子清偿本金,必然会违背农民道义及生存伦理,进而有损自己的社会声誉。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同时不违背农民道义,张吉安把伙友田华轩作为追债对象,显然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