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物价水平可能被严重低估从而导致增长和要素投入数据失真,这是大多数研究结果出现重大差异的关键原因,增长潜力研究也因而严重背离现实。本文通过名义产出与税收之间关系推算了实际物价并调整了经济增速,同时重新估算了要素投入,增加了数据的可靠性。本文研究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仅为8.2%,TFP平均仅增长1.7%,对产出贡献约为21%。但是基于劳动投入估算的TFP结果为-1%,这点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冲击导致要素拉动模式越来越重要,TFP结果被拉低,因而我国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堪忧。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产出虚增
作者简介:张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古明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一、引言
如何正确把握我国的增长潜力是当前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我国转型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研究的核心在于我国增长究竟是要素投入拉动的结果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的结果,亦或是两者都有。如果存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多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增长,这点可以用于对我国增长潜力进行评估。从经典研究文献来看,关于我国增长潜力和技术进步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研究,但是结果差异很大,影响了研究的参考性,因此我国增长中是否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比较乐观的研究认为我国增长中存在相当程度技术进步的成分,否则我国不可能取得如此长期而快速的经济增长。胡和科翰(Hu和Khan,1997)认为我国1979-1994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速高达3.9%,可以解释改革初期40%的增长。罗斯基和伯金斯(Rawski和Perkins,2008)针对我国1978-2004数据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3.8%,可以解释40%的增长。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和Collins,2008)也针对我国1978-2005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3.6%,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达40%的增长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研究结果与帕金斯和劳斯基(Perkins和Rawski,2008)以及胡和科翰(Hu和Khan,1997)的结果非常接近。其它部分比较乐观的研究甚至出现高达45%-58%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麦迪逊(Maddison,1998),樊(Fan,1999)等,这一结果与以技术进步为主的美欧发达国家水平很接近,明显脱离我国发展实际。除以上针对改革初期和中期的研究结果外,部分针对90年代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也出现了较大差异,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和Collins,2008)针对我国1993-2004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同样高达3.9%。在国内,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基于经合组织(OECD,2001)的生产率手册方法,对1980-2002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1980年后大部分年份的TFP为正值,说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率一直在改善。王小鲁、樊纲(200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
与上述研究相反,另外一些研究则持悲观态度,认为我国增长中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并不大,增长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克鲁格曼(Krugman,1994)对我国增长的持续性最早表示了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模式是东亚的一个翻版,缺少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吴(Woo,1998)的研究结果也很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增长率平均只有1.1%。扬(Young,2003)针对我国1978-199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也仅有1.4%,对增长贡献不超过15%。曹(Cao,2009)对我国1994-2000年数据研究结果甚至出现了-0.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国内,张军(2002)的研究也表明1992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世纪之交前后为负值。郑京海与胡鞍钢(2005)的研究结果则更低,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增长率1995-2001年间平均只有0.6%。郭庆旺、贾俊雪(2005)研究也得出一个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增长贡献仅仅为10%左右。
其他部分针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麦迪逊(Maddison,1998)研究表明1978-1995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增长率平均为2.2%。吴延瑞(2008)针对我国1993-2004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表明其增长率约为1.64%-2.94%之间,平均可以解释我国经济总增长的27%。另外,还有部分研究也采用分阶段处理的方法对比不同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差异很大。经合组织(OECD,2005)研究表明1978-2003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以平均3.7%速度增长,但增长率随后逐步下滑至2.8%。王小鲁(2000)研究得出1953-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平均增长率则为1.46%。郑京海与胡鞍钢(2008)研究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年之前每年增速为3.2%-4.5%,但是1995年后每年仅增长0.6%-2.8%。
纵观各类有关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和增长潜力的解释,一个根本争议在于我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究竟是多少。但是当前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研究结果差异非常大,最高结果与最低结果相差数倍甚至十余倍,这点严重影响了当前研究的可参考性。因此分析经典研究差异的根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差异是否符合我国增长实际,并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方法、重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于重新解释我国增长潜力至关重要。本文认为以下几个原因是造成我国增长潜力研究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一)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差异的第一个原因是理论前提和理论假定的差别。
如果学者在研究理论前提中做了某个预期,那么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在数据分析还是在结果整理中就不可避免的朝这个方向去靠近,因此理论前提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于研究结果非常重要。关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解释的理论前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认为我国快速增长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否则我国不可能取得如此快的增速,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从这个理论出发,胡和科翰(Hu和Khan,1997),帕金斯和劳斯基(Perkins和Rawski,2008),博斯沃思和科林斯(Bosworth和Collins,2008),王小鲁、樊纲(2009)等研究得出了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解释了我国40%左右的增长。吴延瑞(2008)、郑京海与胡鞍钢(2008)的研究也得出一个接近30%的平均贡献。另一类研究则从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增长没有生产率贡献,只是要素累积的结果,因此也得出一个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吴(Woo,1998),扬(Young,2003),曹(Cao,2009)等均得出一个非常低甚至为负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很多研究基于我国的长期快速增长就认为这种增长肯定有生产率的很大贡献是不现实的,因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不必然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前苏联发展历程来看,依靠追加要素投入也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另外吴延瑞(2008)认为国有部门改革是生产率提升的一个方面,但是从我国发展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业绩尽管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业绩提升更大程度上是受其垄断地位的恢复,而不是效率的提升。郑京海与胡鞍钢(2008)、吴延瑞(2008)等研究也提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根源。的确,劳动力转移到更有效率的部门是生产率整体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也正因为这种接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导致工业部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升,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力供给过剩、成本非常低甚至免费,这种劳动力供给状况导致工业部门缺乏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的动力,因此期望一个较快的工业生产率增速是不太现实的。
综合来看,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可能太高,过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可能是由于研究假定偏离了我国经济实际从而导致的数据分析误差,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对增长有贡献÷也不可能太高。毕竟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每次一旦出现投资减少或者劳动力短缺,经济随即也快速滑坡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高,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减少不可能对增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最后,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假定的差异也是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因为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要素弹性研究,因此各个学者对该系数假定千差万别,也是造成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
(二)数据不精确、数据浮夸以及口径不一致是造成研究结果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方法和系数假定差别是造成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一个原因,那么这种差别完全可以通过分析各种方法与我国现实经济状况的吻合程度来判断,并且不同研究方法结果还可以互相对比作为参考。另外,大部分研究结果说明资本弹性假定差异尽管有些影响,但并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结果造成较大影响。而传统研究结果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而且系数假定基本相同情况下研究结果差异仍然很大。如邹至庄(Chow,2002,2006),海坦斯和泽布莱格斯(Heytens和Zebregs,2003)等研究基本都采用增长核算法,对于资本弹性假定均在0.6左右,但是研究结果同样差异非常大,研究结果差异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是数据基础的差别。
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影响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对我国统计体系固有的产出虚增是否进行了处理以及处理方式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研究直接采用我国历年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官方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核算资本投入。这种方法存在一系列数据问题,包括我国统计体系普遍存在的虚报增长带来的GDP增速过高、统计体系变化导致的数据口径不一致以及资本和劳动投入核算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并进而影响研究参考性的关键所在。然而传统研究注重了研究方法的改进,试图采用增长核算以及参数和非参数等各种方法找出差异的原因,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数据基础和数据质量的问题,这点主要是由我国长期存在的统计制度不完善、核算体系变化等原因造成的,而且由于对于数据进行调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大多研究避开了这点。
部分研究也注意到了我国的数据问题,并对总产出虚增问题进行了适当调整,这其中比较系统的研究是吴的系列研究(Wu,2000,2002,2008,2011)的研究。吴(Wu,2008,2011)指出数据基础的差别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对GDP增速、就业人数以及其它相关指标进行了一定程度调整,尤其是针对总产出数据采用实物产出指数法进行了重新估算,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研究的不足。但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也会虚增产出的实物量,导致这种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产出虚增问题。其他一些研究,如任(Ren,1997),国家统计局和一桥大学(SSB-Hitotsubashi,1997),劳斯基(Rawski,2001)等也采用不同方法对我国总产出及其增速进行了调整,但是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尽管包括吴(Wu,2008,2011)在内的系列研究重视了我国产出的虚增问题,但是仍然忽视了我国产出虚增的特殊性。我国产出虚增已经并不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而进行的虚夸,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时会对这种虚增进行一定程度的平减,从而抵消了大部分的虚增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认为我国产出虚增的研究结果与官方数据差别不大的原因。我国产出虚增的关键在于深层次的虚增问题,比如价格低估带来的不变价产出的虚增,这种虚增在1998年后出于“物价维稳”的考虑变得尤其严重,而主要研究均未对这点进行调整。
虽然部分研究也注意到了我国的价格低估问题,并尝试基于物价、劳动生产率或者能耗变化对我国总产出进行调整,如麦迪逊(Maddison,1998)、扬(Young,2003)、麦迪逊和吴(Maddison和Wu,2008)。但是这些研究采用国外相关价格和劳动生产率数据变化代替中国相关指标变化并不合适。上述研究没有注意我国发展具有特殊性,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找到与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作为参考,因而借鉴其它国家的能耗变化(罗斯基,Rawsh等)、劳动生产率变化(麦迪逊,Maddison等)或者价格变化(任, Ren等)来判断中国相应指标变化并以此倒推我国真实总产出非常牵强。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所必须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估算的差异也是导致研究数据基础差异以及研究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当前研究针对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以及增长潜力评估必须的要素投入测算也过于粗略,无法反映真实要素投入水平。对于劳动总投入,传统上一般直接采用就业人数变化代替,在计量方法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测量有点过于粗略,无法反映人力投入的质量变化。部分研究采用受教育程度对就业人数进行简单加权的做法仍然无法全面反映人力投入状况,因为人力投入不仅仅是教育一个方面。另外,大部分研究对资本投入的测量也很难反映资本的内涵,且测量所需的某些指标和假定过于武断,并没有说明这些假定的事实基础。对资本和劳动投入估算的不足也是数据基础差异并导致研究结果出现较大误差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我国增长潜力解释的关键仍然在于对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针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产出虚增问题和物价低估问题进行调整,以反映真实总产出的变化,同时系统估算我国资本和人力投入,完善基础指标测算,这样才能科学判断我国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对我国实际物价水平和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投入进行了调整及核算,并重新估算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评估了我国的增长潜力。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主要关于我国生产率的经典研究综述,并指出数据基础差异是造成研究结果差别的原因,因此数据分析和调整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尤其是针对物价水平低估造成的真实产出“隐性”虚增问题进行研究是关键。第二部分针对我国1998年后的物价严重低估和真实产出高估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调整了我国的真实总产出。第三部分针对核算必须的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进行了系统核算,并结合前部分物价水平的估算进一步校正了我国真实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第四部份是本文研究方法体系及相关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是文章研究结论。
二、我国总产出的虚增问题及其调整
综观当前关于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之所以出现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一些研究忽略了我国增长数据和要素投入数据可能存在的数据不真实和不一致等情况,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可靠性差。我国产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我国现有将政绩与GDP挂钩的问题导致GDP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主要一个重要指标,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普遍拥有一种虚报增长的倾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追求导致的名义产出虚增问题;其次,统计口径变化所带来的数据不一致问题可能高估产出增速,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产生影响;最后,中央政府出于“物价维稳”目的低估通货膨胀导致的真实产出高估问题是产出高估和数据不精确的关键。
由于地方政府的虚报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国家统计局平减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因此这一问题尽管存在但是并不是我国产出虚增的根本性问题。针对MPS体系可能产生的增速高估和口径不一致问题,国家统计局和一桥大学(SSB-Hitotsubashi,1997)以及吴(Wu,2000,2008)均已经对上述数据做了系统调整,因此这点也已经不是当前数据虚增的关键问题。因此,当前我国产出虚增的关键问题可能在于国家公布的物价水平可能远远低于真实物价上涨程度,客观上导致不变价产出被虚增。即使从我国30年平均发展来看,很难想象中国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主要物价指数只相对于1978年上涨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倍左右。同时,根据传统研究以及本文的分析,这种物价低估问题主要出现在1998年后(罗斯基,Rawski,2001;孟连和王小鲁,1999),因此本文重点研究1998年以来我国物价和产出可靠性问题。
本文假定我国公布的名义GDP或者真实GDP已经是调整后的总产出,并且国家统计局已经对统计汇总过程中虚增情况进行了适度调整,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估价格水平的失真问题;同时假定我国1997年来我国整体税负水平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政府征税的基础是实际上的名义产出,而不是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政府公布的名义产出其价格水平可能被扭曲,而实际上的名义产出则不存在扭曲,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价格被低估的程度。基于总体真实物价水平等于价格被低估的程度与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之和这一关系,根据我国历年税收收入和名义总产出的变化和我国官方公布的名义GDP变化以及名义GDP平减指数这几个基础数据就可以倒推我国1996年以来真实物价指数,见图1。

由本文估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价格指数对比来看,官方数据严重低估了我国的真实物价水平。1996年以来,我国官方GDP平减指数仅上升了不到1.5倍,这点与人们对物价和消费的真实感觉相去甚远。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以来我国物价快速上涨,GDP平减指数上涨了2.7倍。因此物价被严重低估是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结合上述物价指数,本文进一步对我国1997年以来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并计算了此间真实的GDP增速,见图2。由本文结果与官方公布的结果比较可以看出,1997年以来我国真实GDP增长率年均增长率只有4.7%,即使2002-2009年间增长率也仅有7.5%,远低于官方公布的这一期间10%的增速。其中1997-2001年间出现低增长且出现了两年的负增长状况,这点也比较符合我国都是所处的亚洲金融危机阶段的实际情况,可以有效解释这一阶段能耗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异常变化等情况。因此,我国官方严重低估物价的情况导致总产出被严重虚增和要素投入的扭曲,从而导致以全要素生产率位代表的我国增长潜力研究失去了数据的可靠性。
三、我国的要素投入估算问题
除总产出外,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基础是需要估算资本和劳动投入,并在此基础上估算资本和劳动弹性。对于资本投入,很多研究主要是借鉴现有资本存量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存在概念口径以及核算体系上的误差。对于劳动投入,很多研究则直接采用就业人数。在计量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个指标有点过于简单,难以反映劳动质量的变化。因此,为准确把握各要素在增长中作用,需要对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进行重新核算,这点对于研究结果的参考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一)物资资本存量的核算
关于我国物资资本存量研究尽管已经比较丰富,但是由于研究结果差异太大、标准和口径不统一以及数据续性问题,同时由于对指标把握、分解与资本真实内涵相去甚远,导致其参考性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当前我国资本存量估算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研究前提假定明显不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研究方法也有待改进,选择的代表指标也并不符合资本的内涵,从而导致核算误差:另外,很多研究在价格指数、折旧和基期存量等指标的处理方法上也存在问题,难以符合严格计量前提。因此,针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系统研究对本文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数据基础。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估算并系统改进了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首先,关于核算基础指标。由于资本的含义主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要素投入,而资本形成总额包含部分非生产性投入,因而与“资本”的含义差距较大:就MPS体系下的“积累”指标来说,其数据连续性是一个问题,且会出现重复计算。因此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房产投资等非生产性投入作为生产性资本近似代表指标,分解后数据见“图3”。其次,关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由于国家统计年鉴编制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起点是1991年(1990年为基期),本文采用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出1978-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近似指数。第三,关于折旧。本文采用将各省折旧数据汇总直接得出全国折旧的做法,然后再根据各个省汇总后GDP与全国GDP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得到全国折旧额数据。最后,关于基期资本存量。本文采用增长率法确定基期资本存量,由于1978年之前国有企业是主要企业形式,因此我们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52-1978年期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折旧率计算得出综合折旧率为0.0312,同时计算得出1952-1978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约为0.075。基于这两个数据,综合1978年投资数据,可以得出1978年为基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的资本存量为7528.3亿元,其中生产性资本存量为5696.8亿元。


根据上述指标,结合永续盘存法,可以得出分别以总资本形成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的资本存量,见图4。从基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测度和分解结果来看,我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尤其是生产性资本增速显著大于非生产性资本,表明我国资本积累更重视生产领域。这点也说明传统研究采用的固定资本形成为基础的核算结果与生产性资本内涵仍然存在典型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可能影响结果的精确性。
(二)劳动投入的核算
由于直接采用就业人数或者采用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进行加权调整的方法过于简单,因此基于劳动投入核算劳动投入总量对于本文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当前大多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收入或者基于支出两种方法进行核算。事实上,常用的收入法核算的是劳动投入预期收益,与积累无关。其次,某些研究在投入流量代表序列上采用的指标往往注意了人力积累的“人力”方面,忽视了人力积累的“资本”特性,很难成为理论参考的基础。因此,有关中国劳动投入估算面临很多严重不足,重新估算并分析我国劳动投入总量对于研究结果可靠性至关重要。
首先是选择合适的劳动总投入作为代表指标,我们从分析劳动投入的“资本”特性入手。我们之所以把劳动投入也称之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者“资本”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也是“资本品”的一种,因而也应该符合资本品的共性。根据物质资本核算经验,一个期间有效投资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新购资产的市场价值,二是维持、保养或者进一步提高资产效能的新增投资。
关于人力要素的第一个方面——价格,我们采用劳动总收入代替,即采用就业人员总收入代替市场价格。《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公布了历年就业人员总数和平均工资,但是这种投入忽视了劳动投入的很多方面。比如国家对于居民部门的补贴和转移支付以及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均是劳动投入的效能方面,因此本文均加总后作为人力总投入。另外农村总收入取决于家庭总收入而不是个人工资收入,因此我们采用农村总收入和城市就业工资总额之和作为劳动投入。
劳动要素投入的折旧同样是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物质资本核算过程以及基本会计原理,我们知道新增投资主要是为了弥补损耗以及扩大资本积累。作为一种资本品,人力要素也应该包括市场价值和维护成本(医疗、保健、卫生和基本营养)以及提高资产效能的投资(教育、培训),其中维护成本即医疗、保健、卫生和基本营养的支出主要是为弥补人力资本折旧和恢复人力资本效能进行的投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1952年-2010年全国个人和公共医疗、卫生和基本营养支出(用食品支出来代替)成本来估算人力资本折旧量。
此外估算劳动总投入还需确定基期存量,对此我们借鉴前面物质资本存量核算法确定基期存量,即采用增长率法来确定,这就需要知道这个期间劳动投入平均增速和平均折旧以及1978年劳动投入额。根据基础数据,我们可以得出1952年-1977年我国劳动投入年度增长率平均在0.044左右,折旧率平均在0.047左右,均很平稳,可以作为增长率法的基础。基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1978年我国劳动总积累约为1.9万亿人民币,但是由教育和培训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仅993.7亿元,其中传统劳动投入积累高达1.8万亿元,反映我国改革前追加劳动是劳动投入的主要形式。
在确定了基期人力资本存量、折旧之后,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物价的影响,借鉴物质资本核算的永续盘存法基于支出可以核算出劳动总投入存量,核算结果见图5。由图5看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投入存量快速上升,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与此同时,由要素投入效率来看(图6),我国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ICOR指标在1994年后逐步攀升,反映生产系统的效率可能在下降。

四、方法体系、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本文前期分析,研究方法体系也是造成研究结果差异进而影响研究参考性的重要原因。从当前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主要方法来看,主要有增长核算法、数据包络分析(DEA)、前沿函数以及指数法等几种主要方法。早期主要研究基本采用生产核算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如邹至庄(Chow,1993),波利斯坦和奥斯崔(Borensztein和Ostry,1996),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胡和科翰(Hu和Khan,1997),麦迪逊(Maddison,1998),吴(Woo,1998),艾扎克和孙(Ezaki和Sun,1999)。由于认识到生产核算所基于的不变报酬假定可能难以适用我国实际情况,以后很多研究则采用超越对数以及非参数方法进一步改进了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吴延瑞(2008)等。而郑京海与胡鞍钢(2008)、郭庆旺和赵志耘(2005)以及其它国内相关研究也尝试采用指数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等非参数方法来估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索洛余值、最小二乘计量法以及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和指数法均是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增长潜力评估的经典方法,尤其是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和指数法这些新兴方法在我国生产率研究中比较盛行。但是由于非参数方法缺乏典型统计特征,对于技术前沿面的估算也由于数据精确性问题以及样本容量问题其结果可靠性也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则是非参数方法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数据样本。因此传统的索洛余值仍然是较为可靠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索洛余值法需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本文研究是基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此处生产函数必须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基于上述生产函数进行微分,就可以得出索洛余值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

索洛余值是比较经典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模型,比较适合我国的市场状况。要估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解释我国增长还需要确定要素弹性。本文采用计量方法根据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以及总产出变动得出资本弹性为0.51,劳动弹性为0.49。本文得出的资本弹性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虽然资本投入快速增长,但是劳动投入也在快速增长,因为劳动投入核算的重要基础是劳动收入,因此我国的资本弹性不可能远远高出美国,更不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但是如果采用劳动力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代表变量,那么资本的弹性就上升为0.7,劳动弹性则为0.3,与很多研究的假定非常接近,因为就业人数增加的速度低于劳动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导致以就业人数为基础的劳动总投入存量弹性偏低。
基于要素投入弹性并结合以上对总产出增速和资本、劳动投入增速的调整和分析,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可以得出1979-2008两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见表1和图7、图8。其中图7反映的是基于原始数据进行核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图7看出以劳动投入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3.9%,在相关研究中出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文核算的劳动投入增速快于其它研究所采用的就业人数增速。为对比这种差别,本文进一步采用就业人数增速进行核算,结果见图7。由该图看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高达3.0%,对增长贡献平均高达29.3%,与大多数主流研究得出的结果比较接近。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来看,采用劳动投入为基础的研究结果在1997年后变为负数,而基于就业人数核算的结果也明显下降,这也说明1997年后我国要素投入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的那样,我国1998年后的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物价低估情况,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价格调整后的总产出和要素投入数据进行核算,结果见图8。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我国30年来平均真实产出的增长率约为8.2%,比官方数据低约两个百分点。但是采用本文劳动投入存量基于索洛余值核算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下降为-1%,对增长的贡献为-12.2%左右,这点说明我国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要素投入在我国平均增长中占有绝对地位;但是基于就业人数和调整后产出核算的结果仍然为1.7%,对产出贡献约为21%。调整后数据结果同样说明1997年之前我国大部分年份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出现在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拉动增长而推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要素投入。这个趋势也与大多数研究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只不过本文数据结果相对较低。
采用调整后数据的本文研究结果在相关研究中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并不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贡献不可能为负。从图8看出,我国各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差别很大,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主要来自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9-1991年间生产率的快速下降,这一冲击很可能是政治风波的冲击导致的:第二个阶段的冲击为1998-200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这一冲击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为保持增长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使全要素生产率出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第三个阶段的冲击来自于2007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这一阶段的下降很可能是因为我国政府为应对本轮经济危机而出台的大规模投资产生的。如果将这三个阶段少数特殊年份的冲击去除,则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0.6%,对增长的平均贡献为7.4%。另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出现在1998-2001年间,本文这个阶段的估算结果大大低于其它研究,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增速,一个主要原因是本文对这一阶段调整后的总产出增速非常低,但是调整后增速恰恰符合了我国这一阶段能源和物价等相关数据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调整后总产出数据尽管得出一个长期为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但是却比较符合我国发展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本文之所以出现较低是因为本文对总产出调整后导致其平均增速降低,本文估算的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仅有8.2%,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同时根据要素投入口径调整后,要素投入增速加大,降低了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另外,本文两个结果差距比较大,主要是就业人数并不能反映全部劳动投入,更无法反映劳动质量差距,因此该结果仅仅作为一个参考。采用就业人数和调整后总产出和资本投入估算的结果仍然高达21%也说明了这点。
其它相关研究结果之所以出现一个较大的增长率主要原因在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基础对总产出增速估算过高,同时对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速估算过低,这两者导致了TFP的估算结果比较高。如果在核算资本投入时没有剔除非生产性资本或者存货,则必然高估资本存量从而低估资本投入增速;同时由于我国就业人员收入增速大于就业人数增速,如果在核算过程中采用就业人数为基础进行调整,则必然会低估劳动投入增速,加之1998年后出现的严重产出虚增问题,如果不进行调整其核算结果必然很大。但是这些研究结果无法反映经济的某些阶段性特征,如我国1990-1991年间以及1998-2000年间经历了政治风波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产出应该明显下降,我国为保证产出增速加大了要素投入,在这种双重影响下,全要素生产率应该如本文结果那样出现明显下降,但是主要研究均未得出这一趋势。因此,从本文结果来看,我国30年平均增长仍然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非常低,采用估算并调整后的劳动投入结果甚至为负。
从表1我国各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生产率变动的基本趋势。由调整后数据并基于劳动投入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可以看出,1979-198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平均达到0.9%;1985-1990增速出现下降,为-1.2%:1991-1995年恢复到0.9%,但是随着1997年后大规模投资的出现,1996-2001年间大幅度下降为-3.9%,这一阶段大幅度拉低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贡献。2001年之后,我国的发展目标开始向保增长转向,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要素投入进一步拉低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2002-2008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为-1.1%,这进一步拉低了我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从表1和图7、8看出,我国增长质量下降主要是出现在1998年之后,1998年之前中国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应有的贡献,但是1999年之后我国的增长更多转向要素投入拉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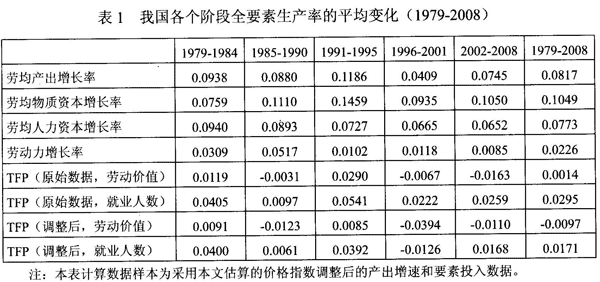
五、研究结论
关于我国增长究竟是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还是要素投入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议,为解决这种争议并改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同时科学解释我国的增长,经济学家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重新进行了估算,但是估算结果差别很大。本文指出即使在采用相同方法体系和系统弹性设定的前提下,不同研究结果差异仍然很大,因此研究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所采用的数据基础不同。数据是否可靠、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研究结果精确性的关键。因此数据发掘和分析调整仍然是解释我国增长的关键,否则任何复杂的方法都只会造成更大的研究误差。当前研究在数据方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没能系统的对总产出虚增情况进行调整;同时,对就业人数的调整以及要素投入的测量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通过对相关数据重新测算和调整,本文得出我国实际经济增速平均为8.2%,因而经济增速被高估是一个事实:资本增速和劳动投入增速则由于口径变化和处理方式差异相应被低估。基于调整后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改革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对增长贡献平均为-12.2%,尤其是1998年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非常明显。从本文结果来看,我国30年平均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非常低,因此我国奇迹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持续下降主要是出现在1998年之后,1998年之前仍然保持平均1.2%的贡献,且大部分时候为正,这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在1998年之前在不断改善,但是两场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家拉动增长的而推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开始持续下降,要素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越来越明显,增长质量堪忧。
因此,传统上认为我国经济增速很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必然很高并无理论和事实依据,因为依靠追加要素投入同样可以带来快速增长。从我国增长实际来看,我国增长对要素投入依赖非常大,投资一旦出现下降经济增速也随之快速下降证明了这点;而如果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素投入下降不可能对经济增速产生如此快速而明显的影响。这些均决定我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可能太高,因此很多研究基于上述情况,假定一个快速增长的生产率作为解释我国增长的出发点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整体来看,数据基础是否精确、可靠并且能够反映我国发展实际对于科学解释我国增长至关重要。我国经济增长在前期比较理想,但是后期随着大规模投资增加以及国有企业重新获得垄断地位等问题的出现,增长质量急需改善,这要求我们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随着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足和资本投入效率的不断下降,这点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2.郭庆旺、赵志耕、贾俊雪:《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3.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4.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5.王小鲁: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讨论[J],《经济学(季刊)》2002第2卷第1期。
6.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7.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J],《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期。
8.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J],《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2期。
9.郑京海、胡鞍钢:《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J],《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10. Borensztein,E.and Ostry,D.J.,1996,“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pp224-228.
11. Bosworth,B.and Susan,M.Collins,2008,“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22,No.1,pp45-66.
12. Cao,J.,Mun S.H.,Jorgenson D.W.,Ruoen Ren,Linlin Sun,Ximing Yue,2009,“Industrial and Aggregate Measur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1982-2000”[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Series 55,Special Issue 1,July.
13. Chow,G.C.and Kui-Wai Li,2002,“China's Economic Growth:1952-2010”[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1,pp247-256.
14. Chow,G.C.2006,“New Capital Estimates for China:Comments”[J],China Economic Review 17,pp186-192.
15. Ezaki,M.and Sun L.,1999,“Growth Accounting in China for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Economies:1981-1995”[J],Asian Economic Joumal 13,pp39-71.
16. Fan,S.,Xiaobao,Z.and Robinson S.,1999,“Past and Future Sources of Growth for China”[D],EPTD Discussion Paper No.53,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D.C.
17. Heytens,P.and Zebregs H.,2003,“How Fast Can China Grow?”[J],In Tseng Wanda,Rodlauer,Markus,China Competing in the World Econom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ashington,DC.
18. Hu,Z.L.and Khan,M.S.,1997,“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D],IMF Staff Papers,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 Krugman,P.,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 Nov./Dec.,pp62-78.
20. Maddison,A.,1998,“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M],OECD,Paris,out of print,available on www.ggdc.net/Maddison.
21. Maddison,A.and Wu H.X.,2008,“Measur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J],World Economics,Vol.9(2),April-Jane.
22. OCED,2005,“Open Market Matter: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M],Paris,OCED.
23. Rawski,T.G.,2001,“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J],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2,no.4,pp347-354.
24. Rawski,T.G.and Perkins D.H.,2008,“Can China Sustain Rapid Growth Despite Flawed Institutions?”Paper for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M],University of Denver,May,pp30-31.
25. Ren,R.,1997,“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26. SSB and Hitotsubashi(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Hitotsubashi University),1997,“The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2-1995”[M],Hitotsubashi University,Tokyo.
27. Woo, W.T.,1998,“Chinese Economic Growth:Sources and Prospects”,in M. Fouquin and F. Lemonie(eds.)[M],The Chinese Economy,Economic Ltd.,Paris
28. World Bank,1997,“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M],Washington D.C.
29. Young,A.,2003,“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pp 1221-161.
30. Wu,H.X.,2008,“The Real Growth of Chinese Industry Revisited”[D],presented at the 30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Slovenia,Aug.,pp24-30.
31. Wu,H.X.,2011,“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in 1952-2008: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 with a Newly Constructed Data Set”[D],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1-E-003,January.
